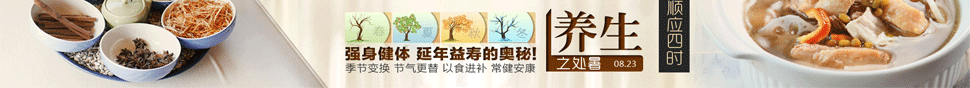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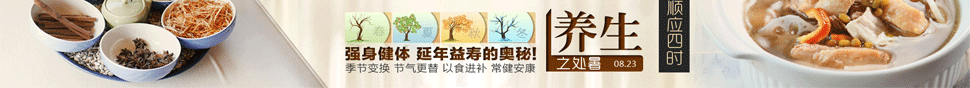
转载自《中国语言学》第三辑,年12月,北京大学出版社。
一
冯蒸教授曾写了一篇讲辞,发表在某刊物年第4期上。他把年开始的那一场以梅祖麟、郭锡良教授为双方主将的争论,称为第3次古音学大辩论。此说可商。上个世纪20年代的那次辩论,真可以说是一次大辩论。牵涉到古音构拟中外对音问题,有着广泛的影响。30年代那一次,范围较小,是一场辩论不差,能否说得上是“大”,尚属疑问。但那两次都在讨论学问,而这一次,即21世纪初的这场辩论与上两次有很大的不同。这一次是由一个外国人发难,得到几名中国人支持的对中国学人的大面积的攻击。他们骂倒清儒,从章太炎骂到王力以及陆宗达、邢公畹,乃至于唐作藩等中国学者。学术上的事当然可以争论,但他们并不就此罢手,而要否定我国的优秀传统,声言中国人没有能耐,只有洋人才行,要由他们到中国这块土地上来“领导”。闻者以为是年以前的事,而的的确确此事发生在年底。所以,这一次是夹带着学术问题的大是大非的争论,也是新时期一次语言学界思想上的大论战。这次大论战现在似乎还在继续。
二
冯教授在介绍了他所说的3次辩论的时间和要点以后,说:“笔者系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汉语言文字教研室主任,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理事,目前已发表了近百篇音韵学论文和多部专著。”
乍听起来,有点儿俗。可一想,亦无可厚非。自炫头衔,以取信于听众,也是常事。说发表了多少论文专著,原本习气如此。现在作个什么统计,或者升个什么职称,或者要报个什么项目(包括奖项),总要有多少篇论文,多少部著作等等,于是乎在讲辞中自我介绍也来这么一套,不足为怪。但讲精神方面的创造力而以多取胜,这个习气并不是很好。乾隆皇帝有诗4万首,王之涣留下来的诗只有6首,你说哪一个是诗人?是有4万首的乾隆呢,还是只有6首的王之涣?
接下来,冯教授说:“——年私淑著名音韵学家陆志韦和王静如先生学习音韵学,师从王静如先生时间尤长。”年,冯教授15岁,中学毕业没有,还不得而知,就开始从名师学艺了,了不得啊。本来的用意是,我从小便是两位音韵大家的学生,我最有发言权,但说得不够明白,到底是“私淑”呢,还是“师从”?倘是私淑,人人得而私淑之,有何可炫?倘是“师从”,又是怎么个“从”法?是于其落难时找空子去登门讨教,人家不得不回应,还是两位大家正儿八经地收你做个学生?
三
冯教授说:他“力求客观地归纳和介绍”双方的观点,也就是说,他将公正地处事,站在不偏不倚的立场。看了全篇讲辞之后,觉得冯教授确实是在“力求”这么做。他介绍双方论点都比较充分,不是一味详此略彼。一些难听的话,也不自己说出,而由他的拥趸捅出。对郭氏与梅氏也各有褒贬,不是专讲一方的不是。与纯以梅氏为宗主的那些人还是有区别的。他这样做事出有因。他的业师洪成玉先生似乎也是北大的校友,属于梅教授所称的“旁支别流”之类。总不便直接和自己尚在的业师对着干吧。但冯教授也听过梅教授半年课,照理也该执弟子礼,况且梅教授是“出口转内销”,正受着某些国人的宠信,自然也不可怠慢。尽管如此,冯教授内心的倾向还是明白无误的。
即如在参加辩论人物简介里,列出4人,郭锡良vs梅祖麟、潘悟云、郑张尚芳,1对3。仿佛一面是人多势众,三人为众嘛,而另一面是孤单一人。这当然是大错特错。站在郭教授一方的是被梅教授所指的“浩浩荡荡”,还有“旁支别流”,“茫茫九派流中国”啊。中国者,国中也,不仅国中,岛上也有,陈新雄教授就是一个;不仅中国,外国也有,薛凤生教授就是一个。我不想代劳,一个一个地列名单,那本是冯蒸教授的事。
前面已经提到,冯教授重论文数量,他的论文“近”百篇,郑张论文“上”百篇,而郭锡良教授只有60多篇。梅祖麟教授“几十年来,对于汉语语法史、汉语声韵学、汉语诗律学均有杰出贡献”,(请注意“均有”与“杰出”,)而郭锡良教授只有一个设想,加上一些影响,虽然这影响很大,那不过是编的教材而已。关于语法史,说郭4个字,“多有创见”,说梅用了8行字,每行40几个字。在冯教授心中,孰轻孰重,不言自明。
更多的论据会在下文中陆续呈现。
四
冯教授把那场争论的分歧归纳为5点,第一点,王力懂不懂同声必同部。在用了整3页篇幅介绍了双方的论点之后,“冯蒸案:王力先生对谐声是重视的。1963年出版的《汉语音韵》都专列谐声表。问题在于他拒拟复辅音,对异部位谐音不能解释。只说音近,太笼统了不科学。又在中古声韵与谐声矛盾时宁从中古声韵不从谐声。例如批高本汉颖是喻四不应与梗荆同族,即不顾及颖是顷声字。”
此案语既有肯定,又指出不足,似乎“公正”了。然而,讲演者在这里却在不顾事实。事实是,梅祖麟教授已经承认他“以前没有读过《古韵分部异同考》(1937),”“妄言王先生不懂‘同声必同部’更是不当。”[1]争论的一方既已承认自己是“妄言”,为什么不介绍出来让受众知情?却用一句“王力先生对谐声是重视的”来蒙混不知就里的人,似乎“懂不懂”还不好说。主将已经服输,而冯教授却还在追加质疑,说什么“问题在于……”。而所提问题是讲声母,与“同部”没有关系。
[1]据郭锡良《音韵问题答梅祖麟》转引,《古汉语研究》第2页,2003年第3期
五
冯教授归纳的争论之二,是上古有无复辅音声母。
冯教授在大体介绍双方的争论要点之后,议论道:王力先生之所以不接受复辅音拟测,是因为依高本汉所拟,声母就会杂乱无章。“郑张依藏文基字前加上加后加的规则提出的复声母‘冠?基?垫’结构,已基本规则化了。”
问题不全在于是否规则化,而在于这些规则能否解释“二合”中的那些离奇古怪的可能的复辅音声母,能否解释多得眼花缭乱的“三合”、“四合”以至于“五合”“六合”。假如不能,规则再好、再有根据也无用。冯教授如果能用郑张的规则对音韵现象加以合理的解释,那就算是问题解决了。只怕是不能。李方桂先生说:“上古时期复声母问题十分复杂,其中有许多现象一直到现在我们仍没有满意的解决方法。”“虽然我们没有肯定的解决办法,但也应当有个尝试。”[1]郑张的“规则”也就是一种尝试而已,而在冯教授那里,好像已是定论,并可以此排除王力先生的担忧,并且进而作为否定王先生对于复辅音的看法的理由,显然是无力的。
既然问题没有解决,那么,王力先生关于复辅音的疑虑,仍然不能排除,他不愿构拟复辅音声母的理由仍然是不能驳倒的。
唐作藩先生对此有很好的论述。我这里引一段:
凡是以印欧语为母语的汉语学专家,都乐于提出或者赞同上古汉语有复辅音,其母语背景肯定起了重要作用。中国的学者了解一些外语(当然主要是印欧语)的,也易于接受复辅音说。我们也必须注意到,反对复辅音说的王力先生,跟没有接触过西学的旧派学者完全不同。王先生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就在当时的世界语言学中心巴黎接受了正规的以印欧语为核心的西方语言学教育,他自己懂得罗曼语族的法语、日尔曼语族的英语、斯拉夫语族的俄语,国内略知印欧语的某些人跟王力先生相比有天壤之别。[2]
[1]李方桂《上古音研究》24页,商务印书馆,
[2]唐作藩《王力先生的“谐声说”》,《语言学论丛》第二十八辑,第20页。商务印书馆,年
六
“一声之转”,是冯教授归纳的论战双方的又一分歧。冯教授以为他归纳的2、4两点是重点,我则认为这一点也就是冯的第三点才是最主要的分歧。因此,我要多说几句,并用来回答梅祖麟教授。
所以承认冯教授还有一定程度的“客观”,就是因为他在这里一字不落地记述了梅教授攻击中国人和中国学者的狠话。梅教授在谈王念孙“一声之转”的时候,说道:“只有清儒才能发明这种论证法,外国人可没有这个能耐。”又说:“王念孙的‘一声之转’,到了20世纪衍生出来一个浩浩荡荡的章黄学派,徒子徒孙,不但有陈新雄、陆宗达等旁支别流,还包括邢公畹、王力、唐作藩、刘钧杰等。”[1]
梅教授本学数学,后来转行,搞语言是半路出家。在国外,这条路子可以走得通,在中国就难了。因为在中国,搞语言学,总怕要读一点基本书,其中包括王念孙的《广雅疏证》,连这本训诂基本书都没读,而敢侈谈中国的语言学,岂非笑话?梅教授自己承认,他只是听人讲了讲《广雅疏证》,就来大放厥辞了。在中国人批评了他之后,他是否去读王念孙的书,不得而知。恕我妄测,他或许还没有读,或许读了,一时难以读懂,又放弃了。最好的猜想,是他已经读了,心有所得。只怕这种可能性不大。不过,我还是从最好的方面来揣度人,让我来说说对“一声之转”的理解,以与梅教授交流。
《经义述闻》卷三“明听朕言”
家大人曰:《尔雅》:孟,勉也。“孟”与“明”,古同声而通用。(《大戴礼·诰志》篇曰:“明,孟也。幽,幼也。”明、孟同声。幽、幼同声。《豳风谱》正义引郑注《书传略说》曰:“孟,迎也。”《北堂书钞》引《春秋考异邮》曰:“明庶风至,明庶者,迎众也。”《禹贡》“孟猪”,《史记·夏本纪》作“明都”。)故勉谓之孟,亦谓之明。《盘庚》曰:“明听朕言,无荒失朕命。”言当勉从朕言无荒失也。《顾命》曰:“尔尚明时朕言”,言当勉承朕言也。《洛诰》曰:“明作有功”,言勉作事也。又曰:“公明保予冲子”,言公当勉保予冲子也。《多方》曰:“尔邑克明,尔惟克勤乃事。”言尔邑中能勉行之,尔则惟能勤乃事也。《韩子·六反》篇曰:“使士民明焉尽力致死,则功罚可立,而爵禄可致。”言勉焉尽力致死也。重言之,则曰“明明”。《尔雅》曰:亹亹,勉也。郑注《礼器》曰:“亹亹,犹勉也。”亹亹,勉勉,明明,一声之转。《大雅·江汉》篇:“明明天子,令闻不已。”犹言“亹亹文王,令闻不已”也。《鲁颂·有駜》篇曰:“夙夜在公,在公明明”,在公勉勉也。
“家大人”是谁,想必不要我解释。不过,考虑到有人对古汉语基本著作的陌生,还是不厌其烦地说说。《经义述闻》的作者是王引之,“家大人”即王引之称其父王念孙,故所引例仍属于王念孙的“一声之转”。我们看看他怎么个转法。这一条的意思是解释“明”有“勉”的意思,“明,勉也。”分3层来证明。第一,以通用字类推。“孟,勉也。“孟”与“明”,古同声而通用。”所以“明”有“勉”的意思。“同声”指原本同声,即是一声之转。声即音。“同声”是理据,“通用”是事实。在括弧里(原文用夹行小字)举同声与通用的证据。第二,从语料中归纳。引古书中6例,其中“明”都是“勉”的意思。第三,以同义重言词比照。这里正是说到“一声之转”,因为“明”与“亹”的读音虽不同,但它们都是原于同一个音而产生的时间或地域的变体。务请注意,这里“一声之转”也是理据,而非证据。“明明”与“亹亹”同义并不是因为“一声之转”,而是由比照而得。
我们一再说,“一声之转”不是论据,而是理据,解释此词何以有此义的理由。当然,由于经常使用,也有可能出现比较简单的形式,而其总体确实只是理据而已。“明”何以有“勉”的意思,因为它们音同音近,有时可以代用。就是不说这个理据,“明”的“勉”义也确凿不磨。同时,“明”有“勉”义,又反过来证明,古音二字字音有相近的可能。《广雅疏证》的主旨是证明此词有此义,列出古文献为据来证明它。我们讲尊重人,也包括尊重古人,王念孙在这里作了贡献,我们就承认他的贡献。如果没有他的劳作,我们到现在还可能弄不明白“糵、鼃、葎、昌、孟、鼻、業”等字有始的意义。而谈“一声之转”是证明此词何以有此义,是锦上添花。后人应当感谢乾嘉时代这项发明,开拓了人们的视野和智慧。我们要知道王念孙他们所处的历史条件和认识条件,他们在讲“一声之转”的时候不能不带有局限性。但不可因此而否定全部“一声之转”,进而否定全书,进而否定全人,再进而否定所有谈“一声之转”的后人及其研究成果。况且也不可以简单地对待“一声之转”,抱着为我所用的目的来评价它。我们下面看看一些较为多样的情况。
《史记?灌夫传》:“武安已罢朝,出止车门,共韩御史大夫载,怒曰:‘与长孺共一秃老翁,何为首鼠两端?’”[2]《后汉书?西羌传》:“月氏来降,与汉人错居,虽依附县官,而首施两端。”[3]一说“首鼠两端”,一说“首施两端”,“鼠”“施”一声之转,而鼠、施既不同源,韵部也相隔较远。
《楚辞?(宋玉)招魂》:“吴歈蔡讴,歌大吕些。”王注:“歈、讴,皆歌也。”《文选?(陆机)吴趋行》:“四座并清听,听我歌吴趋。”吴歈、吴趋,一声之转。
《楚辞?(刘向)九叹?忧苦》:“山修远其辽辽兮,涂漫漫其无时。”王注:“辽辽,远貌。”《诗?小雅?渐渐之石》:“山川悠远,维其劳矣。”笺:“其道里长远,邦域又劳劳辽阔,言不可以卒服。”正义:“广阔劳劳之字,当从辽远之辽。”辽、劳一声之转。
《淮南子?修务训》:“诚得清明之士,执玄鉴于心,照物明白,不为古今易意。”《魏书?甄琛传》:“伏维陛下,纂圣前辉,渊鉴幽慝,恩断近习,宪轨维新,大政蔚以增光,鸿猷于焉永泰。”[4]玄鉴、渊鉴一声之转。
诸例所转词语,都不同源,且音韵或近或远,不是非要声韵皆同皆近不可。
而有人把“一声之转”片面化,一音之转就要是同源,就是要声韵皆同。他们本想抓一把现成货来研究同源词,现在利用不了这些材料,就愤慨起来,以为那东西一点用处没有,于是他要骂人了,清儒竟如此之轻率,方法竟如此之简单,代代相传师承不变,外国人哪有这般能耐?
真正说起来,外国人真没有法子能像王念孙那样做学问,包括梅祖麟教授。不但要求掌握王念孙的方法,要对古音韵的地位有确切的了解,还要对古籍烂熟于胸,信手拈来,便成文章。前无古人,后世呢,不是说没有。有也是凤毛麟角。外国人更无从谈起。把梅祖麟的反话作正面理解,倒的确如此。然而,梅实实用的是挖苦的话。他在轻蔑一个民族。他的轻蔑又正是这个民族复兴之时,岂能容得?
做过清华大学17年校长的梅贻琦先生,当年对他的学生说:“诸君在国外的时候,不要忘记祖国;在新奇的社会里,不要忘掉自己;在求学遇到困难问题的时候,务要保持科学态度,研求真理。”如果梅先生地下有知,他也不会满意他的不肖子孙。
瑞典人高本汉,研究汉学,特别是中国的语言学,至今为止,洋人似无出其右者,而对中国人的尊重,也堪称模范。他是我们的好朋友。近日读到马悦然的文章,我来引一段:
高本汉充分意识到他自己作为学者的价值,但同时,他总是时刻乐意表达对古今中国学者的感激之情。在《中国音韵学研究》的中文译本的序言里,他首先对清朝的伟大学者们表达了敬意。接着阐明了现代中国学者的贡献:“一个西方人怎么能梦想和他们相比?这班现代中国学者完美地掌握文言和整个中文典籍世界,完全可以以把他们的研究活动扩展至整个中国文化领域,而西方人唯一能作的事情,就是使自己努力熟悉这一领域的一个小角落,并在那做出他的些微贡献。这样,他仍然能够为他所仰慕和热爱的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这个文化,略尽绵薄之力。”[5]
高本汉总不忘表达他对“古”“今”中国学者的感激之情,他认为一个西方人只能在这个领域的“一个小角落里”作出“些微”的贡献,他“仰慕和热爱”这个国家、民族和文化,梅教授扪心自问,你有这种可贵的情怀吗?
可怪的是,冯蒸教授介绍到此,竟无半点反应。仿佛骂了该骂,“一声之转”真的就十恶不赦似的。他说他要“客观”,这就是他的客观!恰如鲁迅先生所说:“不是上帝,那里能够超然物外,真下公正的批评。人自以为公平的时候,就已经有些醉意了。”[6]
还是接着讨论梅教授对中国“一声之转”的不满吧。他举太炎先生《文始》中的例子,来证“一声之转”的不当。不了解中国学人对太炎先生的感情啊,这怎么和一个外国人解释呢?
鲁迅先生论太炎先生时说:“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7]太炎先生《告本师》的节概,制订注音字母的功劳,《新方言》继二千年之绝学,《文始》开中国词源学的先河,炳炳琅琅,岂容抹煞?
我见闻有限,不知道有什么人在哪里说过太炎先生学术上的不是。不是没有见到,而是不愿去说。中国人的感情就是如此。近年思想开放,情况有所变化。也开始有人有所涉及了。但那说法,与梅教授完全两样。比如节于今先生,他在文章里说:“章太炎先生实是我国现代语言学的前驱,他的“语基”说,他的《文始》就是一个创新。创新的东西不一定完善,不一定成熟,这就需要完善。太炎先生所用的只据语音相通来确定同源词的作法,显然不够科学,需要完善。后继者不能补阙,反而守着这个不科学的老套套,这就很难说是后出转精,是创新了。”[8]比一比梅、节两家的说法,看得出来对同一事实的完全不同的看法。这就是中国人和非中国人的区别。看到了太炎先生的某一点不足,梅教授如同捡到了一个法宝似的用来攻击中国人。中国人不是没有看到,只是情感各各不同。
王力先生写《同源字典》时,对前人这方面的工作和不足,有所借鉴。他指出其不足在于:“在语音方面,则通转的范围过宽,或双声而韵部相差太远,或叠韵而声纽隔绝;在字义方面,则展转串连,勉强牵合。”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多半是指太炎先生。他为什么不直指《文始》呢?这就是外国人不能体会的那份对尊者的感情。为了避免前人的敝端,于是王先生“在语音规律上严加限制”,“大量引用古人的训诂,来证明不是我个人的臆断”。[9]亏得梅教授苦寻,终于从《同源词典》中找得了一个韵部较远的例子。《同源字典》曾经说到“荒”、“薉”同源。[10]而“荒”在阳部,“薉”在月部,语音上似乎相隔较远。
王先生已过世,没有办法起之于地下而问之。王先生举此二字同源,必有其理。郭锡良先生曾以“荒”“薉”本有通转关系来解释。要我来回答,又可能要惹得梅教授出来骂人。不过,既是事实,就不怕指责。事实是,只同声者也不是没有同源的可能。正如孙雍长教授所言:以为“同纽之故而得通转者往往有之”,“于音理言固然有欠周密,但核之于文献语言,音转多由于双声者确为事实,这是不容抹煞的”。[11]这个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视而不见,决不是一个好办法。
那就请举出事实来。我就从大师的著作中举例。
王国维《尔雅草木虫鱼鸟兽名释例》:“……其词或为双声,或为叠韵,此物名之大略也。”[1]在“双声”之下,夹行小注:“如薢茩,芵茪。蘱,薡蕫之类。”后文对这两条注作出了解释。“又《释草》:薢茩,芵茪,蔆,撅攈。案:薢茩、芵茪、撅攈,皆有圭角之意。薢茩,郭注以決明釋之。決明,秋生,子作角。而蔆亦有角,故得芵茪、撅攈之名。蔆之亦名薢茩,亦以此矣。”[2]此言薢、芵、撅同声母,可得相转,茩、茪、攟声母近,可得相转。“蘱,薡蕫”,王国维说解如下:“又《释草》:蘱,薡蕫。案:薡蕫,长意。郭璞说‘薡蕫’云:其叶似蒲而细,是长叶之草。又《释天》之‘螮蝀’,其字从虫,本是虫名。沈方伯说以《庄子》‘蝍蛆甘帯’之‘帯’,虹形如带,故以‘螮蝀’名之。是‘螮蝀’‘薡蕫’,亦语之转矣。”[3]此言“螮”“薡”声母同,可得相转。看了这些话,也许梅教授余怒未息,也要把王国维大师骂为章黄之流了。
[1]王国维《观堂集林》——页,中华书局,
[2]同上,页
[3]同上,页
讲音转学说重视声母,当始于钱大昕,其言曰:
“近”既从“斤”,当以其隐切为正,其读“几”者转音,非正音也。如“硕人其颀”亦“颀”之转音。《礼记》“颀乎其至”,读“颀”为“恳”者,乃其正音耳。“倩”从“青”而与“盼”韵,“顒”从“禺”而与“公”韵,“实”从“贯”而与“室”韵,“怓”从“奴”而与“逑”韵,皆转音。《礼记》“相近于坎坛”,郑康成读“相近”为“禳祈”,“祈”未必不可读为“近”也。[15]
所谓“转音”,即一音之转。钱大昕又说:
《小旻》“是用不集”,训“集”为“就”,即转从“就”音。《鸳鸯》“秣之摧之”,训“摧”为“莝”,即转从“莝”音。《瞻卬》之“无不克巩”,训“巩”为“固”,即转从“固”音。《载芟》之“匪且有且”,训“且”为“此”,即转读“此”音。[16]
与梅教授同在商务出书的,有一位郭晋稀先生,兰州大学教授,他的书名《声类疏证》,多页,他举例证明组字,多因双声而转,你能说他没有根据?他是字字有根有据,不然,怎么会叫“疏证”呢?我们“一声之转”知道得太少,去翻翻这本书,开开眼界。如果因此又生出一番骂来,我倒是很乐意再听它一听。
由于“一声之转”,梅教授说,衍生出了一个浩浩荡荡的章黄学派,徒子徒孙。他把章黄学派看浅了,也看低了。从数量来说,他又估高了。你以为章黄学派是那么容易做的吗?章黄的要求可高着啦。第一,要饱读诗书。湖南师范大学的周秉钧先生,到北师大讲课,与当时的青年教师王宁接谈,他问王:你十三经读了几部?[17]读完13经,这是章黄的一个起码要求。第二,要能写一手像样的文言文。我曾经用文言写一篇学习心得给我的老师看,我的老师可是正宗的章黄,他把我骂得抬不起头来。我从此再也不敢写文言,从此再也不敢做章黄。第三就更难做到了,不轻易写东西。他说你爬还没有学会,就想要跑了。读好书再说。这3条我一条都没做到。十三经中的三礼,我“视若蛇蝎”;写文言,虽不敢勉强对付;而写文章,我却轻率了,没有“近百篇”,更谈不上“上百篇”,却也有好几十篇。所以,你不要怀疑我是章黄的徒子徒孙,我不够格。真正的章黄也不会承认我是章黄。曾经有人自称是章黄门生,可章黄的人就是不认帐,认为他太浅薄,怎么可能是季刚先生的学生?
有了这3条,还加上一定的仪轨,这才能成为章黄学派的人。可你想想,当今之世有几人能合乎这3条?不论大陆,台湾,够条件的都不多。又从哪里来的“浩浩荡荡”?
我得声明,这3条并不是我的章黄老师所说,他没有这样明说,凡与章黄学派挨点边的人,大概也没有听老师们这样明说过。这只是我一人的体会。积数十年之经验,我深信我的体会没有错。有一年,举行黄季刚先生逝世若干年的纪念会,我亲耳听主持者说:黄焯耀先先生[18]一再叮嘱,不要讲章黄学派,章黄在学术上有过一些影响,但并无一个学派。我体会耀老的意思,是要听过章黄学派老师的课的人,不要自外于整个学术大军,以赶上时代的步伐。也是鉴于真正能如章黄那样要求的学人几乎已经没有了,尊崇朴学的章黄不能接受这个徒具的虚名。
章黄学派并不等于听过章黄弟子讲课的人,听过课的人不少,但能称得上是章黄学派的人则极少,因为时移势异,不可能按章黄的办法来教学,也不可能按章黄学说来教学。请查查中国高等学校使用的古汉语教科书,有哪一本不是将章黄学说只当做一个历史现象来表述?如果能查出有一本书将19纽28部作为最终的上古音学说,那我就不与你争论了,我服输。现在把听过章黄弟子的课的人都叫做章黄的徒子徒孙,不管他够不够章黄,不管他信不信章黄,那当然是“浩浩荡荡”的了。你就不怕这个“浩浩荡荡”都起来反击你的不实之辞吗?
批评黄氏古音说的首先是林语堂,而批评得影响最大的是王力先生。有他的《黄侃古音学述评》[19]为证。可他又怎么也成了章黄的“旁支别流”了呢?因为章太炎的《文始》讲一声之转,而王力先生的《同源字典》也讲“叠韵”“对转”“旁转”甚而至于还有“通转”,所以被梅教授认定是一路货。可王先生讲“转”,有严格的语音限制,有点不如梅教授的意,可也被找到了一个语音较隔的例,以一代众,由于王先生不直属章黄一系,所以想出了一个“旁支别流”的话,也算煞费苦心了。王先生一生在教书育人,又长期在中大北大等名校任教,所教学生本多,名气大,威望高,影响广,击倒章黄之后,再把王力一系连带击倒。中国语言学界也就差不多了。可还有漏网之鱼,又把邢公畹也扯进来,邢先生从事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和汉台语比较研究、语言理论研究、汉语语法研究,不知在什么地方也得罪了这位洋大人,也成了章黄的“旁支别流”了。只怕是因为在章黄与王力之外,还有他人,就取邢公畹作代表吧。这样,除了梅教授所认定的“主流”而外,至少是历史语言学界,已经洪洞县里无好人了。
在批了章黄的徒子徒孙与旁支别流之后,犹觉不够解恨,补充道:“章黄学派算不算有中国特色的语言学?当然不是——因为它根本不是语言学。”为什么不是呢?他没有进一步说。承前而言,或许又是指那个“一声之转”。如果不是指用“一声之转”来任意解释词义,它本身并无不是。转者变也。语音难道不是流动不居、因时因地而变化的吗?而“转”是有规律的,所说的“一声之转”是按规律在“转”,此话一点错误都没有。至于《文始》中的瑕疵,如王力先生所说,“则通转的范围过宽,或双声而韵部相差太远,或叠韵而声纽隔绝”,但也不能因此就否定全部“一声之转”。要知道《文始》所用的通转规律,大致上还是不差的。它的不足在于未经证明就断定一组词的同源性质,并不是它的通转规律出了什么大问题。况且,章黄学说也不是一个“一声之转”所能概括。你听听李方桂先生怎么说:“清朝出了很多大学者,如:顾炎武、江永、孔广森、朱骏声、江有诰,一直到后来的章太炎先生,黄季刚先生,对上古音的研究都有很大的贡献。我们的研究只能利用他们的材料,另外用一个新的方法去研究它。”[20]
[1]站在梅教授的立场上说话,这些话要作些修改,应改为:“……不但包括陆宗达、陈新雄等,还有王力、邢公畹、唐作藩、刘钧杰等旁支别流。”
[2]《史记》2853页,中华书局,1959
[3]《后汉书》2899页,中华书局,1965
[4]《魏书》1512页,中华书局,1974
[5]马悦然《瑞典与中国的知识交流》,张振江译,《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页,年第3期
[6]《华盖集?并非闲话(二)》
[7]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
[8]节于今《建设创新型语言学》,《古汉语研究》第3页,年第1期
[9]王力《同源字典?序》第2页,商务印书馆,
[10]同上,页
[11]孙雍长《音转研究述要》,《河北师院学报》——页,年第4期
[12]王国维《观堂集林》——页,中华书局,
[13]同上,页
[14]同上,页
[15]《潜研堂文集》卷15《答问十二》
[16]同上
[17]王宁《答谢恨晚——怀念我的老师周秉钧先生》,《古汉语研究》增刊第1页,
[18]他是黄侃季刚先生的侄子,武汉大学教授。
[19]据我所知,此文先在香港发表,后来收入《龙虫并雕斋文集》第三册。
[20]李方桂《上古音研究》96页,商务印书馆,
李先生接下来就列出高本汉上古声母表如下:
这圈出来的15个声母,只有在介音j的三等韵前出现,别的声母可以在任何韵母前出现。李先生说:“在全体34个声母中,几乎有半数的声母分配很特殊,很有限制。这使我们对这15个声母发生疑问。”[1]李先生进而推论,只有那19个声母,才可能是上古音的声母。我们审察一下,这19个声母,便是季刚先生的19纽,它们依次是帮、滂、並、明、端、透、定、泥、来、精、清、从、心、见、匣[2]、疑、晓、影。
照黄侃的说法,1、4等是古本音,2、3等是今变音,所列19母能拼1、4等,其余各母不能,故它们是古本音。而李方桂先生采纳了季刚先生的学说加以完善,说章黄学说就根本不是语言学,这又从何说起?太炎先生没有证明一组词同源,只凭语音推论,可以提出批评;而你说章黄学说根本不是语言学,难道不加论证就可以信口雌黄吗?
对于梅氏这番不留任何情面的歼灭性的扫荡,冯蒸教授仍不忘装出一副公正的样子,说:“梅氏的批评伤人太重,打击面过大。”那就是说该伤,伤得重也可以,只是太重了些,比如说,可以说章黄的学说不是语言学就可以了,不要说成“根本不是”。打击面大了也无妨,只是过大了,比如说,可以讲衍生出一个章黄学派徒子徒孙就可以了,不必前面还加上“浩浩荡荡”。至于冯教授此后还加上了几句伪善的话,就不必再提它了。
本来该说的话说完了,但还有余意。梅氏骂了中国人,又差不多骂尽了中国的历史语言学界。前面都是辩诬,现在也来回他几句,来而不往,非礼也。当年吕老主持的语言所,觉得有个懂外国的中国血统的学者来研究汉语,有不同的视角,于汉语研究有利。以我堂堂大国,岂不能容一个梅祖麟这样的人物?虽则成就不怎么样,但也不是一个门外汉[3]。而梅贻琦先生当清华校长多年,为清华现在的发达和地位奠定了基础。对于梅校长的追思,也在情感上为梅祖麟教授进入中国语言学圈帮了不小的忙。北大当时的看法与语言所相同。于是给他发文章啊,帮他出集子啊,请他讲学啊,参加学术会议请他发言啊,奉为上宾。一个语言所,一个北大,这两个地方竞相抬捧,梅祖麟就这样在中国这块土地上,飞黄腾达起来。王力先生与吕老相继谢世,而梅祖麟教授在中国形成的这种气势有增无已,并且因为群龙无首,这时的梅教授已忘乎所以,不知道自己在中国语言学界的正确位置,已摸不到自己的后颈脖在哪里。于是乎目中无人,骂倒一切,仿佛中国这块领地,他已十拿九稳了。他离开生他养他梅氏家族的故乡太早,太不懂得中国的历史,不懂得中国人为了不受外国欺侮,进行了怎样艰苦卓绝的斗争,不懂得中国悠久的历史创造了何等灿烂的精神文明,不懂得中国的语言学者有过辉煌的业绩和不懈的努力,也不懂中国人民所怀有的对于外敌入侵的深刻的记忆和一再压抑着的本所当有的情感。梅祖麟在外国人面前,他是中国人,他懂得中国;在中国人面前他是外国人,他懂得外国。借中国之崛起自重,亦借外国的强盛而自傲,而骨子里却还是中国人懦弱可欺,他的祖国亦即美国全球无敌。这种内蕴,这种不祥的心态,在他年年底的讲演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一个疏于读中国书的外国人武断地否定了一声之转,有几个脑子不能自己作主的人也在那里鄙薄一声之转了。我想对这些人说一句,想否定一声之转是徒劳无功的。就在前年,即年,郭、梅之争发生后的第4年,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香港两位朱教授的书,叫做《中国佛籍译论选辑评注》,那里就多处谈到一声之转,或者实际上说的是一声之转。即如62页上说:“译者释也”,“所谓翻译就是解释。”这不明明说的是一声之转吗?不烦到他处去找,即在同页,又说“胥通疏”。“胥”何以通“疏”,那理据没有明说出来,如果说出来,也当就是一声之转。巧得很,同页又有如下的话:“雅言里的‘鲜’,到齐国方言里变成了‘斯’:鼻韵尾掉了(元音开口度也变小了)。……传统音韵学把‘鲜’变为‘斯’称为‘一声之转’,或‘阴阳对转’。”可知香港两位理工大学的教授,也并无鄙薄一声之转的意思,讲训诂也还是离不开这个“传统”。
本来我已经说过,在讲一声之转的时候,即算是王念孙,也有局限性,后人在运用一声之转的时候,更不乏缺点,但总体上是不可否定的。学无根柢的人,还有紧跟外国邪风的人,越是否定它,我就越是要讲得响些。我之所以要特别在这里回应一下梅祖麟教授,就是因为时下有人在没头没脑地跟风,有不得已于言者。
[1]同上,12页
[2]李氏认为匣应并于群,故有此标注。
[3]从梅教授在商务()出的书来看,他那样的文章,在中国大陆,能写出来的人不说有几百个,几十个总是有。然而只有一个得宠者,自然离不开他的背景。
(未完待续)
编辑、排版:笔谈组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